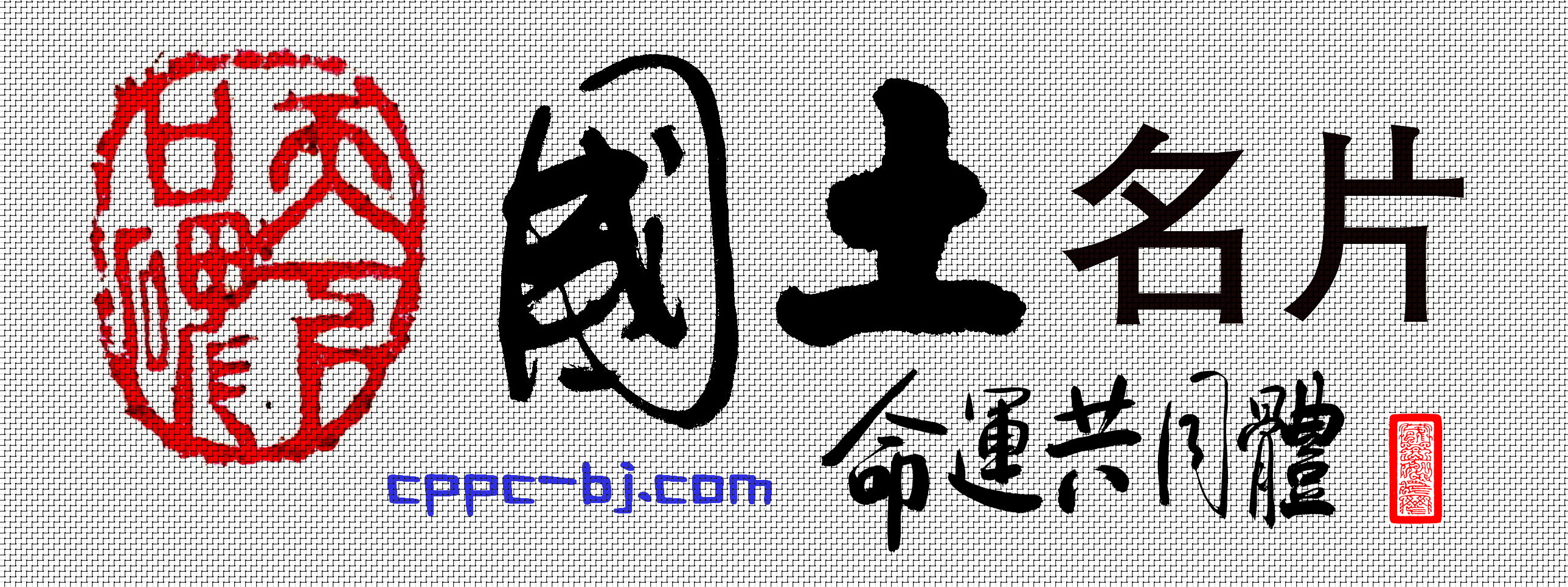
共同体与现代性
《外国语文研究》杂志 2023年1期
【文学理论前沿】 主持人按语:“后理论时代”如何重新激活理论?
在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中,特里·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作为理论在英语世界的旗手和重要推动者,伊格尔顿的“倒戈”自然引发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理论持一种更为警醒的态度。当然,这里的理论主要指于20 世纪60、70 年代开始兴起的文化理论,其时的政治失利使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正蓬勃兴起的文化事业,试图为推进现实政治寻找新的资源和开辟新的路径。但在发展过程中,理论越来越与现实政治脱节,这种凌空蹈虚的理论更多成为了一种时尚的知识消费品。伊格尔顿对这一现象的批判,与其说他是在“反对”理论,不如说其目的是为了重新激活理论,让“去政治化的”理论重新政治化,从而更好地介入现实。当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同样引发了诸多问题,理论本身的针对性、复杂性和局限性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出现简单挪用、随意曲解和“强制阐释”等不同形式的滥用。但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理论本身的历史性以及当下理论的“滞后”。理论无不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或社会现象的反思、总结和提炼,现实的变动不居决定了理论的历史性,一旦现实发生变化,既有的理论就不仅很难对现实进行阐释,甚至会成为阻碍。新的社会现实需要新的理论对其进行图绘、阐释和指导,如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联系的日趋紧密,全球性的协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人类同样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危机,这都需要理论去回应。与此同时,以暴力、战争和领土占领为特征的殖民主义已走向终结,种族关系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都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下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显然不能再简单地挪用萨伊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的理论。此外,社会结构的变革给当代女性带来了新的挑战,之前的女性主义理论同样已很难阐释当下女性面临的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就必须不断地自我更新,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话题,绘制新的理论版图,才能让患有“政治贫血症”的理论再现生机,更为强健有力地介入现实,而本期的“文学理论前沿”栏目中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共同体;现代性;雷蒙·威廉斯;“相同性”;让-吕克·南希
作者简介: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文研究》副主编,目前主要从事英语文学、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但这一话题在理论界的热度始终未减,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概念背后的积极意蕴。从词源上来看,共同体的拉丁语名词为communitas,前面的com 是“ 与、一起”(with, together)的意思,后面的名词unitas的意思是“ 統一”(oneness, unity),整个词指的是以平等、团结和温情为特征的共同体。更具体地说,共同体是指生活在同一地方的一群人,因为有着共同的习惯、兴趣和文化等,他(她)们都能找到归属感,彼此能和谐相处,相互扶助。关于共同体传达的这一积极意蕴,英国学者雷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进行过描述,他指出,共同体这个英文词在14 世纪就已出现,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它(共同体)有‘ 直接、共同关怀 的意思;另一方面,它指各种不同形式的共同组织,而这些组织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充分表现出这种关怀”(Keywords 76)。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则将共同体同社会区分了开来,在他看来,共同体成员之间有着更为亲近、紧密和更有胶着力的联系,而社会的形成则更多是以特定利益为动机。因此,共同体是“ 现实的和有机的”,而社会则是“ 思想的和机械的”(52)。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同样将共同体视为温馨的存在,其成员相互依靠,他还总结说,“ 共同体总是好东西”(1)。由此可见,作为对更为理想的、和谐的和值得向往的社会形态的描画、希冀或构想,共同体还蕴含着道德、价值和政治上的判断。
共同体的维系取决于其成员心中的认同和归属感,就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而言,既需要一些客观方面的条件,但同样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条件可以包括地域、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亲缘关系等,威廉斯曾对共同体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这包括:1、平民百姓或普通人(14 至17 世纪);2、国家或有组织的社会,后者相对较小(14 世纪至今);3、同属一个地区的人(18 世纪至今);4、共同拥有某物的特征,如:利益共同体、商品共同体(16 世纪至今);5、对拥有相同身份和特征的感知(16 世纪至今)(Keywords 75)。不难看出,威廉斯这里提到的主要是共同体的客观方面,就主观条件而言,还可以列入文化、传统、信仰、时代精神和个人兴趣等。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指出,对现代共同体的“ 想象” 不仅得益于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和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同样有赖于“ 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45)。就这番话而言,同样可以看出共同体既有客观存在的一面,同样有其主观建构的一面。根据分类标准的不同,共同体有不同类型,但不管就哪一种类型的共同体而言,主客观方面的条件在建构共同体“ 共同性” 的过程中都不可或缺。
在共同体研究热潮的背后,是现代社会引发的焦虑,正如鲍曼所言,“ 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对幸福生活而言,这一品质至关重要,但我们栖居的这个世界却越来越不能提供,甚至越来越不愿意给出承诺”(144)。在现代社会,高效的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大量农民开始流离失所,不得不进入城市,成为工厂中流水线上的工人。在这一过程中,之前自给自足的乡村共同体开始分崩离析,陌生人社会开始取代之前的熟人社会。被驱离故土,再加上城市生活的变动不居,使得现代人普遍找不到归属感。城市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现代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体的把控能力,每个人都感觉自己不过是社会这架庞大机器上的零部件。金钱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驱动力,在这一大环境下,现代人越来越理性,更为注重利益和实效,人们在相互交往时于是多了些算计,而少了些温情,人际关系开始变得冷漠。总而言之,现代社会充满了流动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亦即鲍曼意义上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现代社会整个儿地处于永远的变动中,每个个体都只不过是过客,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因此同样强调,在资本的驱动下,为获取更多的利润,生产就必须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因此始终处于动荡和快速的重组之中,不断的破坏、创造和更新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最终结果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恩格斯 31),没有什么可以提供长期的寄托。现代社会带给人们的是无根感、碎片化和不确定性,自然会招致不少人的批评。
有趣的是,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在英国却引发了两种相对立的关于共同体的态度。首先是批评的声音。在这一阵营中,文化理论家利维斯(F. R. Leavis)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利维斯将“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视为理想的社会形态,并籍此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批评。在利维斯眼里,在“有机共同体”之中,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自然都能够和谐相处。在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之中,人可以得到全面发展,劳动并不是因为强迫,而是可以带来满足感的自我实现形式。总体上来讲,利维斯推崇的是一种小规模的、农业的和前现代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只存在于过去,在现代社会注定会烟消云散。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不仅批判了利维斯意义上的这种怀旧式的共同体,同时还将现代性视为进步的力量。在威廉斯看来,对“有机共同体”的浪漫化想象,对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其内部的黑暗面和诸多问题避而不谈,其目的是为了粉饰建立在压榨、剥削和等级制度上的封建社会。虽然不留情面地批驳过利维斯礼赞的“有机共同体”,但威廉斯同样将共同体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威廉斯这里,过去那种“直接的”共同体是非连续的、破碎的,是前工业社会的遗响。现代性并非一种具有威胁性的力量,教育程度的提高、语言的标准化和大众传播等都是塑造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的重要“资源”,因此需要立足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重新构想共同体。①以传播为例,在威廉斯看来,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共同体理论,传播是人们根本的存在方式,只有通过传播,个体的、独特的经验、经历和意义才能转化为共同的经验、经历和意义,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才会不断丰富、成长和壮大。在威廉斯看来,随着现代传播手段的横空出世,共同体事业已有了极大推进。由此可见,以充满“ 乡愁” 的笔调,利维斯缅怀的是一种已经逝去的共同体形式,其视角是“ 回顾性的”,其理想中的共同体和当下社会形态相对立,这种共同体存在的现实基础已土崩瓦解;而威廉斯则以当下为着眼点,他希冀的共同体对当下社会形态持肯定的和赞扬的态度,在他看来,一种以平等、交流和成长为结构性原则的共同体正在途中。
作为文学批评家,威廉斯还提出过“ 可知共同体”(the knowable community)这一概念,共同体在这里成为了意识形态的“ 试金石”。在威廉斯看来,事物的可知性不仅取决于被认知对象的特性,与此同时,同认知主体的视角也有很大关联。对“ 可知共同体” 背后的主观因素的发现,充分体现了威廉斯文学批评的创新、力度和高明之处。共同体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着其能否被认知,但与此同时,在作者描画的文学空间中,“ 什么是可知的,不仅仅取决于客体本身所具备的功能——有什么是可以去被认知的。它同样是主体或观察者的功能—— 欲求的是什么,以及什么应该被知道”(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 17)。这一点在简· 奥斯丁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奥斯丁主要关注的是英国的乡绅阶层,而将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困难从她描画的“ 乡村共同体”之中抹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威廉斯高度评价了狄更斯、布朗蒂姊妹(the Bront?sisters)、乔治· 艾略特、哈代、康拉德、乔伊斯和劳伦斯等作家,因为这些作家不断将更为宽广的、更丰富的和更完整的社会图景带入文学空间,从而让读者了解到更为真实的现实。
在容纳和维持内部秩序的同时,共同体还暗含一种排斥性机制,将各种异质性因素控制在疆域之外。威廉斯阐明了内在于共同体之中的这一运作机制,他的分析不仅指向现实中的共同体,同时还指向文学空间中呈现的共同体。德里达(JacquesDerrida)同样对共同体的运作机制进行过分析, 在他看來,任何共同体都遵循着免疫和“ 自身免疫”(auto-immunity)的双重逻辑。通常而言,免疫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当病毒或外来细胞入侵身体时,免疫系统能够迅速将其识别出来,并产生出抗体来排斥、破坏和摧毁这些“ 入侵者”,维护身体健康。但免疫系统同样会出问题,有时会产生抗体来对身体本身进行攻击,危害自身的健康,例如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这种“ 自杀式的” 行为严重时还会导致人的死亡。在德里达看来,共同体的运作同样遵循着这一双重逻辑,“ 共同体意味着一种共同自身免疫性(com-mon auto-immunity):任何共同体都会形成其自身免疫性,献祭式的自我毁损的原则在不断破坏自我保护机制的原则(维护自身完整性,使其不受损害),这是着眼于某种不可见的和幽灵般的幸存(sur-vival)”(51)。换言之,共同体的免疫系统会保护共同体不受外来者的入侵,共同体内部的纯洁性总是以对陌生人、“ 外来人” 或“ 他者” 的排斥和伤害而得以维持,但“ 自身免疫” 则会针对和伤害共同体自身,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
这一自我毁损的自身免疫共同体(self-destructive autoimmune community)给美国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提供了灵感,在他看来,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中就存在德里达论及的这一逻辑,这不仅体现在作品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中,同样体现在塞丝(Sethe)和自己的女儿宠儿的关系中。在这部作品中,塞丝将宠儿视为自身最美好、最纯洁和最为珍贵的一部分,但为了不让她落入到白人的手中,遭受欺压和凌辱,塞丝最后选择将其杀死。在米勒看来,这一逻辑不仅存在于虚构的文学作品之中,现实世界的运作中同样存在这一逻辑。在德国纳粹统治期间,反犹主义导致了大屠杀,而包括大屠杀在内的多种因素最终促成了第三帝国的灭亡。除此之外,奴隶制、美国的“反恐战争”和网络共同体等背后都存在这一逻辑,在对众多例子进行分析后,米勒总结说,“每个共同体在试图摧毁入侵者的同时,也产生自掘坟墓的自毁倾向”(316)。在德里达和米勒这里,共同体的运作机制远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在容纳、温情和团结的同时,同样还存在着拒斥、冷酷和自我伤害,由此可见,如果采取更宏观的视角的话,就会发现共同体并非“总是好东西”。
总体上而言,上面述及的共同体观念有以下共同特征:首先,对共同本质的确信。这些观点将某种共同的本质作为共同体的基础,这种本质可能是某种共同的现实基础,亦可能是某种共同的精神维系,包括语言、地域、职业、社会阶层、种族、制度、传统或理想等,这种共同体要想得以维持,共同体就必须将自身封闭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利维斯和威廉斯构想的共同体相去甚远,但他们构想的共同体都以同一性为目标,后者的共同体不过是前者的放大版而已。或者换言之,利维斯礼赞的是乡村共同体,威廉斯却准备以一个充分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其次,对宏大叙事的坚持。此类共同体往往会忽略自身内部的差异性,而将某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奉为终极目标,认为目标的实现即意味着所有人的幸福。最后,压制性。为维持自身的纯洁性、完整性和圆满性,并达成目标,共同体不仅会压制来自内部的各种不同声音,同时还排斥陌生人或“他者”,正如鲍曼所言,“共同体意味着‘相同性(sameness),而‘相同性则意味着‘他者的不存在”(115)。关于这一点,米勒同样强调说,“一个友爱(fraternal)的共同体——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其形成乃是在于排斥异己,反对那些不是同胞的人,反对那些不参加圣餐仪式的人……此类共同体的团结建立在驱逐和排挤上”(33)。而要彻底抹除“他者”,往往还会涉及到对暴力的使用。这一共同体的思考理路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危险性同样明显,那就是这种对共同本质、同一性和宏大叙事的坚持,再加上对“他者”的排斥,将会导致不宽容、对“他者”的迫害和极权主义。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不少理论家都在试图构想另一条思考共同体的路径,以超越上面论及的各种局限性,在这一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有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以南希為例,正是认识到了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是失败,在《非功效的共通体》(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一书开头,南希就指出,“ 现代世界最重大、最痛苦的见证……就是对共同体的消解、错位或焚毁的见证”(1)。基于这一认识,南希构想的是一种以“ 非内在性”(non-immanence)为特征的共同体,其成员是独体(singularity),而非个体(individuality)。在南希看来,作为共同体成员,每个独体都拥有“ 隐秘的他异性”,独体间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同样不可能形成一个总体性的主体,因此,南希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从未真正存在过,其只能是以缺失的形式而存在。不同于前面述及的共同体,由独体组成的共同体的基础是“ 存在—于—共同”(being-in-common),这种共同体并不是由某种内在的本质所定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体就是抵制本身,即对内在性的抵制。因此,共同体就是超越,不过这‘ 超越 不再具有任何‘ 神圣的 意义,而只是精确地表达对内在性的抵制”(Nancy 35)。这种共同体是非功效性的,不可能成为类似于政党之类的实体性存在,因此不可能服务于任何政治目的。由此可见,南希意义上的由独体构成的共同体“ 从同一性转向差异性,从确定性转向偶然性,从封闭转向开放”(Delanty 104),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前面论及的共同体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但这种对任何政治实体的不信任同样会带来问题。因此这两种路径都不对米勒的胃口,因为在他看来,“ 一个共同体要么是由于外界隔离而相互关联的人群构成,要么可能由彼此无甚关联的人构成”(41)。米勒因此构想了第三种共同体模式,这一模式“ 将一个既有社会视为多种共同体的集合,这些共同体之间彼此交叉、相互联系,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完全隔绝在其他共同体之外”(41),这种复数的共同体是对上述两种思考路径的中和。
总而言之,共同体是一种“ 乡愁”、一种批判的视角,同样是一种社会理想。面对现代性的冲击,重新激活共同体是为了重新寻获在现实社会中无处找寻的温情和归属感,对抗社会中人和人关系的物化,建构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对现代性导致的缺失进行批判。但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共同体却可以指向不同的社会架构,导向不同的政治后果。尽管关于共同体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但就其复杂性而言,共同体研究还是一幅刚刚打开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