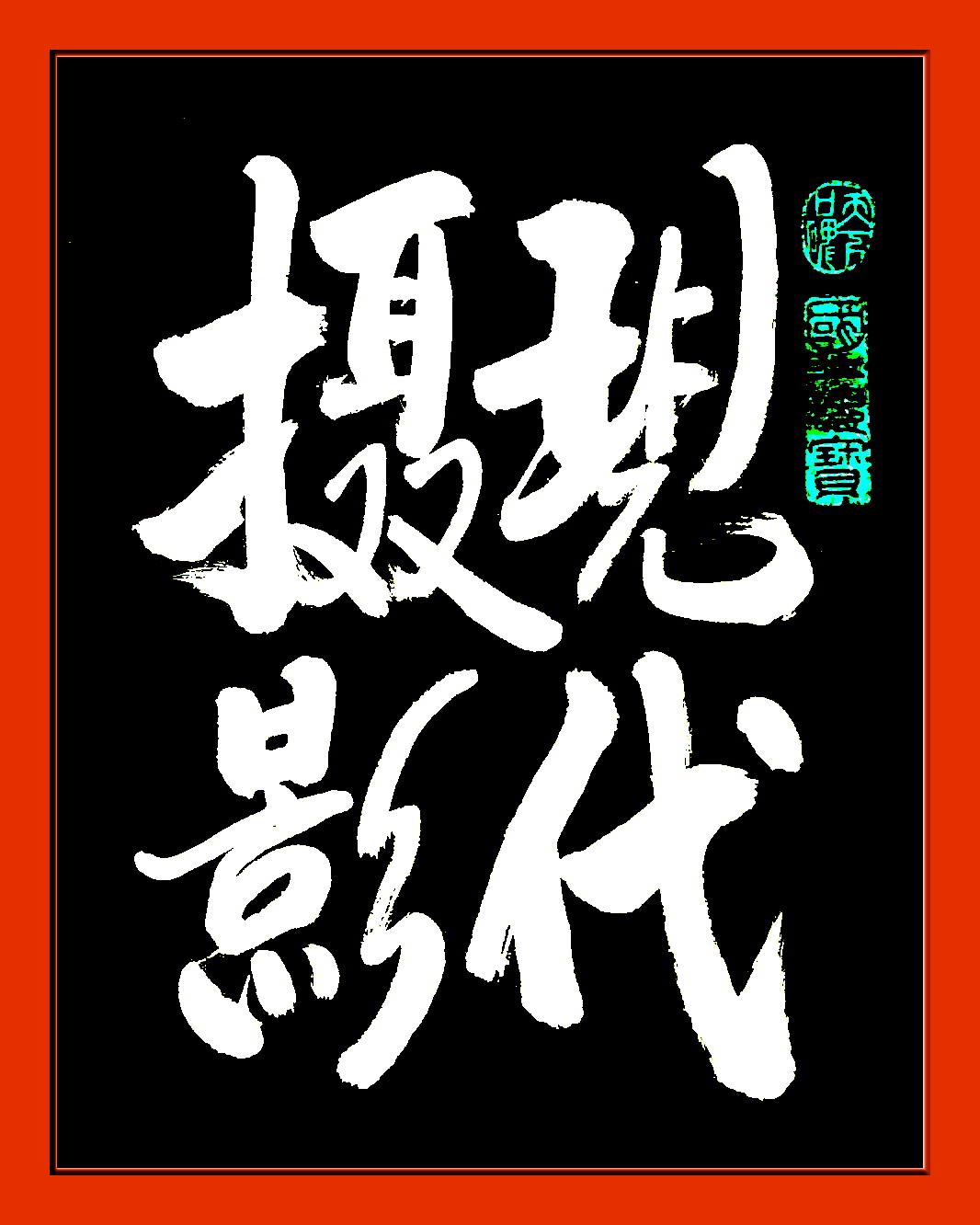
乔惠民书(原现代摄影编辑部主任、焦点杂志首席记者)
来自: 关山 2011-09-18 14:00:21
原标题:
李媚:做一本理想艺术杂志的年代已经永远过去了
导语:她曾经改变了整个1980年代中国摄影界,她曾经是当代纪实摄影的旗帜性人物。但她现在已不大记得当年的宏大叙事,抖落的只是悉悉索索的一地鸡毛。
文/朱慧 图/马也
(李媚:1980年代至90年代摄影界的大姐大,著名先锋杂志《现代摄影》、《焦点》的灵魂核心;当代纪实摄影的旗帜性人物。)
两次约李媚采访,她都在生病。她的声音很北方,也有些有气无力的“柔和”。被问及一个大事件的年份,她转身唤丈夫帮她想想,一声“老X,哪一年的事儿”隔着走廊飘过去,你能发现岁月笼罩在那个下午,有些苍凉。李媚用“最好的年代最辉煌的年代”,为自己的1980年代定了基调,说到如今的自己,声音止不住地往下沉着。
回忆性的采访让李媚陷入岁月,有些不能自拔。一打开话闸,在当年那段纪实摄影大讨论中风头甚健的李媚不再记得宏大叙事,抖落的只是一些特别煽情的细节。此一刻的李媚,实在像大家回忆中,那么“凶悍而凛冽”。
有些摄影师爱说的一句话——李媚改变了我,比如说这话的有肖全,是李媚提醒感性的他放弃某宏大题材,立足女性题材摄影;韩磊,在做《现代摄影》美编的时刻,把自己的照片和版面一起挂在墙上被李媚慧眼识英雄;王征,因为李媚赠送他一本张承志的《心灵史》而找到了自己影像中的“西海固”在摄影界一炮而红……同时被李媚改变的还有李媚。
《新周刊》:怎么会加盟《现代摄影》?
李媚:1984年2月的时候,苗小康和我提及《现代摄影》,他说要做一本给年轻人看的新杂志,这本杂志将进行一切和摄影有关的探索和寻找。他希望我加盟这本杂志,劝我说,你来深圳吧,深圳赚钱很容易,你很快就能自己买尼康相机了,这对我而言是个诱惑,所以,我去了。
我记得自己是在开始拍照两年后,1975年的时候,自己买了第一架相机,200元的海鸥。在深圳我没有赚到尼康相机的钱,后来苗小康送了架尼康相机给我。
《新周刊》:当时摄影界的现状如何?
李媚:那个年代,民间很少有人能拥有相机。照片对人而言是有神秘感的东西,摄影师是在被尊重、崇拜的。当时的主流摄影是唯美派的政治宣传,就是类似东方日出、黄山松树、炼钢工人英姿……那样宣传画似的图片。慢慢的,类似香港摄影家陈复礼等被引入中国。这个以唯美风格标立的休闲摄影家,他的风光、静物和人物摄影,得到了中国摄影官方的极大肯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一时间,被称为"沙龙摄影"的摄影风格风靡一时,成为那个年代官方半官方影展上的"风格宠儿",备受推崇。
1979年,“四月影会”出现,标志着除主流摄影、沙龙摄影外,民间还有第三种“摄影”,就是纪实摄影。民间纪实摄影人在探索中寻找先锋刊物,应该说《现代摄影》是在那种状况之下应运而生的。
《新周刊》:整个1980年代摄影先锋的一个“热词”是什么?一切的发端就是“四月影会”么?
李媚: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时,我想没有一个词能像"纪实"那样有号召力,能唤起摄影家对中国现实的关注甚至参与。“四月影会”发起者中有“四五运动”的摄影骨干多人,影会举办的第一回影展前言开宗明义:“1976年的4月,丙辰清明,一伙年轻人拿起了自己简陋的相机,投身到天安门广场的花山人海中。一种使命感促使他们勇敢地拍摄下中华民族与‘四人帮’尖锐斗争的珍贵文献资料。“1979年的4月,以这伙年轻人为主筹办了这个艺术摄影展。大家在新的领域里,又开始了勇敢的探索。
当时的四月影会确实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开始,它倡导了一些观点,比如“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内容不等于形式;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还比如“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等等”......在那个年代都有一定意义。?
《新周刊》:记得你自己最初怎么踏上摄影道路?何时发现你再也不能举起相机?
李媚:我最初1970年代被安排在贵州安顺文化馆工作,领导安排我拍照,就此进入摄影之门。当时对摄影震撼的感觉不是来自于按动快门的一刻。而是洗照片,影像显影出来那一刻的喜悦。我加盟《现代摄影》的时刻,还一心想着要拍好照片。那时我曾经得过全国女性摄影金奖,是拍母子情,还是以人性为主题的。一做杂志就发现不能拍了。看了那么多图片接受那么多图片资讯,我的头脑被无限打开了。但是手脚被束缚了,再也不能举起相机。
我记得1984年的时候,我有机会重新拍东西。当时贵州电视台想召我过去做专题拍摄。当时我觉得自己还是热爱亲自上阵拍摄的人,因此作出离开杂志社的决定,可是当我回头看见办公室里那摞厚厚的读者来信,我忽然改变决定,不走了。
《新周刊》:能否介绍一下8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摄影展览?
李媚:1980年代中期,陕西一批中青年摄影家发动了一个尖锐性的全国摄影评选,并组织了大型展览《艰巨历程──中国摄影四十年》。这是一次尽可能还原历史和确立“人是摄影主体”的努力,他们展出了一批尘封的历史和反映现实的照片,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的平常,但在当时从摄影家手里找出那些照片就已经让他们费尽了周折,披露了一批造假的新闻照片,评出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照片并使这些照片得到了传播的机会。主办者所写的宣言是:我们力图在甘与涩的交融中整体地把握复杂而撞击人们心灵的世相。力图用一种文化意识概括而集中地审视与映现几经苦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命运、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希望。
这个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策划这个展览和评选的组织者,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出生于50年代(共和国第三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中国纪实摄影的主要基调。
其实当时我们做《现代摄影》杂志,就是被使命感和责任感所驱使的。
《新周刊》:1980年代的摄影书籍,你会给我们推荐哪本?
李媚:80年代末有两本书值得一提,一是《摄影》丛书,一是《中国感受──一个摄影家的1988-1989》,都是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摄影》丛书的第二辑就是纪实摄影专辑,编者明确提出了纪实摄影的问题,并批评了中国摄影的现状。《中国感受》应该说是中国较早的一个以图文并行的方式进行公众传播的文本。1988年出版社请了两位摄影家和一位文字作者对中国(除西藏外)做了一次全景式的扫描,作者与出版者都怀着一个愿望:做一个中国民生文本。遗憾的是,无论是书的图片文字还是社会影响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出版社的尝试和摄影家的努力都是值得记下一笔的。
《新周刊》:作为先锋摄影杂志,《现代摄影》是否主持过一些摄影展、一些摄影讨论?
李媚:1986年时,《现代摄影》与《中国摄影》之间有过一次民间与官方的争论,争论的系列主题是关于摄影的思想解放、个性化,摄影是否是对社会生活记录与反映;图片是应该歌颂美好的,还是表达客观残酷等等。
1992、1993年,《现代摄影》组织过探索摄影大奖赛,在大奖赛上列举了很多摄影观念,那是对80年代摄影探索的一次总结。比如与当时文学同步的伤痕摄影、寻根摄影,现在看来当时列举的很多摄影观念都是没有观念的观念,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新周刊》:《现代摄影》创刊后反响如何?
李媚:第一期卖得特别好,1万册全卖完了。当时做杂志也特别没有规矩,买完了,想想就再版吧,又印了1万册。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说《现代摄影》改变了他们,天天都有几拨读者来编辑部“朝圣”,我们习惯了上班时刻,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编辑部,很热闹,像个家。
《新周刊》:记得当时你和杨小彦有一段著名的讨论,就是“不能给历史留下空白”?
李媚:当时,我和杨小彦说起了林永惠,这个东北的摄影家原来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时,林永惠作为一个军人摄影家,是现场唯一的见证人。可是,在那个歌颂英雄无视现实的背景下,摄影家林永惠没有把镜头对准一幕幕灾难的场面,他只关心符合宣传口径的对象,结果他错过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致使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难没有留下历史的影像记录。这就叫做给"历史留下了空白",这是摄影的遗憾,更是影像的耻辱。“空白"问题就成了那几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后来更演变成一篇宣言似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我们当年的信念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希望用影像来书写历史,而且是用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更不是"唯美"的独幅照片来书写历史。我们那时强烈地认定摄影家的工作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摄影家的日常工作就是用影像为身边从而为历史留下逐年逐月的记录。摄影家的工作不是那样的,拿着高级的摄影器材,然后出去"寻找"拍摄的题材和令人感兴趣的对象。在这样一种情绪下,《摄影》的主编方向当然就确定为"纪实"。
《新周刊》:《现代摄影》是做到第32期终结的,那一期做的是什么内容?如果当时知道那是最后一期,你会如何安排内容?
李媚:当时,做第32期杂志时,我们并没有想到那是最后一期,是一个结束,《现代摄影》第32期刊登院校学生的作品。这个巧合特别好,正好暗合《现代摄影》〉版成《焦点》,这样的转折是杂志的新生。
最初做《现代摄影》时,我们只认为摄影的功用是记录和表达的。其实摄影是对生活的叙述,这时纯艺术类杂志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表达功用,因此我们想做本类似《LIFE〉那样的社会类杂志。
如果当时知道是最后一期,也许会做一期回顾,总结,会集中刊登一些读者来信,会告诉读者这不是终刊,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
《新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国外摄影作品?刚接触时有什么感受?
李媚:在《大众摄影》打工的时候。在那儿有机会看到在贵州根本无法看到的国外的照片。看了许多的展览,比如蒙克的版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北京,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大口袋,如饥似渴,生吞活剥的把所能看到了往里装。最初最深刻的印象是:照片还可以这样拍!
我对摄影的认识是和当时的思想、文化解放思潮联在一起的,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至于对纯影像的认识,我想大多与天生的素质有关。我是个比较敏感的人。
《新周刊》:你与同时代摄影者的关系?最好的朋友是谁?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什么?
李媚:在深圳办《现代摄影》的时候我对朋友们说过,其实办杂志是我与这个世界交流的一个借口。这个世界是一个隔膜太多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人与人的交流往往需要理由,需要机会,需要借口。其实在办杂志的整个过程中,我最看重的是借助着它,我获得了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的机会,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一些朋友。有些甚至是一生的朋友。那时候的人际关系真好,真干净,真真诚。大家都对理想与信念有着执着的追求……
朋友们给了我许多的温暖、力量、理解与智慧。尤其是在深圳的那些日子,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是朋友们的帮助支持着我。记得1985年快过春节时的一天,深圳基本成了座空城,街道突然一下特别冷清,人们都回家了。我坐在办公室呆呆地望着窗外冷清的街道,心也空得无处放置。突然送信的送来了十封信,十封朋友们的来信!那天傍晚,我把那十封信紧紧地抱在胸口从办公室走回宿舍……
《新周刊》:你似乎一直都特别在意读者来信?
李媚:记得《焦点》停刊,我离开编辑部的时刻,我唯一拿的东西是整整一箱的信。当时我先生已经来北京了。我也马上要离开深圳来北京。我知道没有特别情况,深圳将不再是我的城市,我的杂志生涯就此结束了。我清楚记得那天的夕阳,不是太浓烈,也不是太惨淡,很平常的黄昏,有一点感伤。我想那些读者来信是那些年岁月最好的纪念。我记得当时《现代摄影》是最贵的杂志,每本1元9毛,有读者寄来100元,当时这是一大笔钱,他说希望《现代摄影》是长命百岁的,他想预订到100期,当然杂志最后只做到了32期。《现代摄影》终刊,很多读者都特别难受,有人说,我的精神生活被终止了。
《新周刊》:肖全在《我们这一代》中有张拍你的照片,那是在哪里拍的?
李媚:我在深圳近20年,办公室一直在桂圆街131二楼。这只是一幢普通的80年代老楼房的一个普通的房间,一点点在日新月异的深圳中变老。外面有条老街,看得到街上人来人往。记得搬离桂圆街时,我有预感我马上会离开这座城市。
肖全在桂圆街的街道上给我拍照片。那张照片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我的背后站着一个人,刘香成。因为他的提议,牵线促成了《现代摄影》与白马公司(当时《焦点》投资方)的合作,改刊《焦点》的诞生。对《现代摄影》的杂志命运而言,他是一个特别的人。
《新周刊》: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你特别凶悍?
李媚:我是急性子的人。当时《现代摄影》这类杂志如何生存一直是个问题。我们当时还有自己的影楼,拍照挣钱养活杂志。我要管经营筹钱,管内容,管出版,整天连轴转特别辛苦。最忙的时候,有次我得了过敏症,因为所有抗过敏药吃了都会睡觉,我没时间睡觉,就撑着,不敢吃抗过敏的药。
《新周刊》:1980年代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李媚:80年代对我而言是最美好而辉煌的年代。80年代是有文化激情、理想的年代。那个年代有革命性的基石,非常可贵,有建立精神气质的可能。而现在的一切是畸形变化的。我们当时想拥有个性的思维生活,现代人都有了。除缺个性理想之外,社会理想是一个人永恒的价值观,而现代人的这一块是缺失的,一切的发展都很失衡。
《新周刊》:你如何看更年轻的一代摄影人?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人。你会给现在的青年摄影者什么忠告和奉劝?
李媚:他们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我特别希望与他们交流,成为他们的朋友是我的荣幸。我无权对他们提出忠告。
《新周刊》:离开《现代摄影》,你觉得自己还可能做本杂志么?目前,你在做什么?
李媚:我已经不可能再做一本杂志了。
去年我曾经在做《东方艺术》的改版工作,当时拿出一个改版方案,我自己特别喜欢。我一直很喜欢两本杂志,一本是《生活》,另一个是本主题摄影杂志《DU》。该杂志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做东西,比如一个事件,一种颜色,一种状态,当时《DU》发现了著名摄影师桑德。这次《东方艺术》的改版,我是模仿那本杂志样式来做的。投资方最终不能接受。
我想做一本理想艺术杂志的年代已经永远过去了。
旁白:
1980年代初,中国北方的摄影人正在酝酿摄影在新时期的第一次纪实运动------“四月影会”的发起者们以明确的政治立场(也包括部分的形式主义审美立场)介入摄影,他们的激进作为努力恢复着摄影媒介作为历史证言的社会功能,打破了摄影长期以来作为政治宣传机器的疲弱格局。
进入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图片库中开始有了普通人的影像和真正意义的市俗生活。中国摄影的镜头开始转向了民众,转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转向了摄影家自己对生活感受的表达,转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自觉记录。
这个时期民间和官方的摄影活动最为频繁,各地的摄影组织、群体也非常多。1984年,《现代摄影》在深圳创刊,创办人为当年广州“人人影会”的苗小康。这个杂志逐步以先锋的姿态影响了至少两代中国摄影人。杂志的灵魂人物李媚日后还以深圳为基地,主持了《摄影》、《焦点》等多个专业杂志的编辑工作。这几本杂志以国内同行鲜有的先锋姿态发掘、介绍了一批日后为国际所重视的中国摄影师,也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国际摄影界的动态和国外摄影大师的作品和文献,为1990年代中国摄影多元化的发展做了重要的学术准备。此外,杂志社本身还培育出了一批重要的摄影师,如韩磊、王宁德、亚牛、杨延康、肖全等人——虽然他们当年在杂志社的工作并不是拍摄照片。
美术批评家杨小彦在这一阶段也参与了《摄影》等杂志的主编工作,他也是国内最早涉猎摄影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之一,在这些杂志上杨小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摄影文论和艺术家访谈。1988年第一期《摄影》杂志刊发的《拍摄这个动作……——与张海儿对话》一文,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当代摄影的访谈文献,其中涉及的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镜头的权力问题,成为摄影界、艺术界探讨至今的话题。《摄影》丛刊第2期(1989年1月)还刊登了“纪实摄影专辑”,这也是对中国的纪实摄影这一现象做出的最早的集中介绍。
当时1980年代值得关注的还有80年代中期大型展览《艰巨历程──中国摄影四十年》,在展览后所出版的画册《中国摄影四十年》的前言中,编者这样写道:“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摄影的主体。《中国摄影四十年》着力于揭示‘人的主题’,正因为如此,《艰巨历程》和它以前的任何一个摄影展览都拉开了距离,标志着中国的摄影终于规模性地以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与历史和社会对话了。
在《艰巨历程》展览之后不久,纪实性的照片因其《艰巨历程》的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的摄影界渐渐形成影响和规模,一些摄影人开始将自己的镜头从沙龙式的摄影转向了具有历史人生的内容。“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一专有名词才真正慢慢地被国人接受并使
